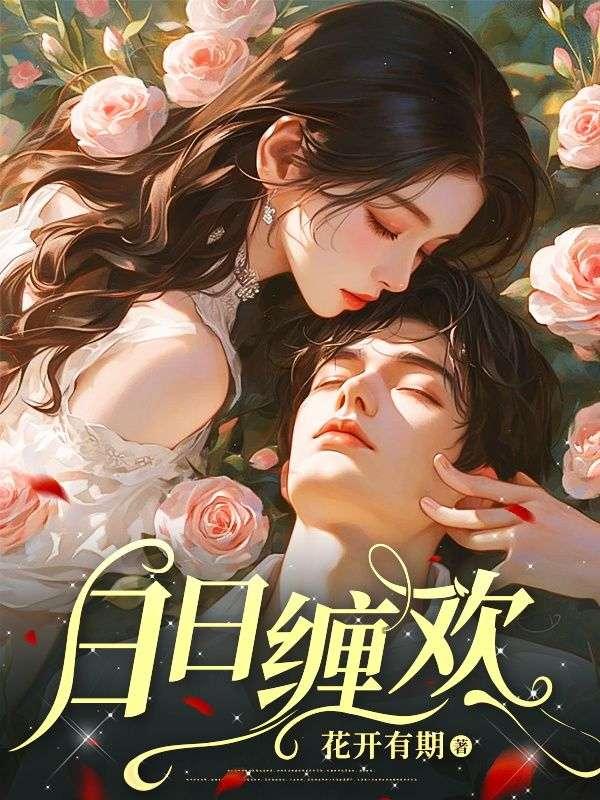落秋中文网>女主对她情根深种[快穿] > 150160(第17页)
150160(第17页)
秦央挪了挪身子,空出一半位置来:“老调重弹……算了,我不想讲,你自己过来看吧。”
陶宁摘了官帽,毫不客气地往秦央身边一坐,借来奏折只看了第一眼,啪的一声合上:“算了,我不认字。”
龙椅只能坐皇帝一个人,旁人不能轻易冒犯,否则视为大不敬。
这大逆不道场景却无人觉得奇怪,宫人们各自眼观鼻鼻观心,美人灯似的站在原地。
朝中上下大家都知道,陛下只跟永远不升官的大理寺少卿好,如夫妻一般。
这大理寺少卿也是奇怪,天底下没有谁能做到她这样,与陛下举止亲密,还能劝得动暴怒的陛下,都说她是陛下的入幕之臣。
可她却与旁的入幕之臣不同,她不需要高官厚禄,也不需要封侯拜相,从初绽头角开始,只守着大理寺少卿的位置不肯挪窝。
住也只住跟皇宫隔了两条街的府邸,那还是以前的太傅府,他老人家一生清贫,虽简在帝心,住的清贫,她让人修缮好了,也没好到哪里去,就这么将就住着。
一住就是五六年。
功名利禄不放在心中,难不成,还真是见鬼的真情了?
这处处尔虞我诈的地方还能容得下真情?
秦央笑了,随手翻开一本,扫了一眼内容,故意递到陶宁眼前问:“我们满腹经纶,明察秋毫的少卿大人还不认得字吗?”
陶宁收下这本催婚奏折,合上放在一边,转移话题:“今年恩科状元,长意瞩意谁?”
她不是不想与秦央大婚,只是还不合适,时机未到。
这些年秦央做的事情不少,忽然冒出一个大婚,能把这群臣子吓撅过去。
秦央总觉得愧对于她,可在陶宁心中心意相通更重要,不急于一时。
万事过犹不及。
秦央哪里听不出她的意思,就是在转移话题,她只管大理寺里的事情,外头翻天了也不管,怎么可能会有兴趣问新科状元姓甚名谁,是圆是扁。
这种探听圣意的事情换另一个人八个脑袋都不够砍的,而宫人们早就从第一次的震惊到现在的见怪不怪。
果不其然,秦央也不隐瞒,直接说:“工部尚书次女,杜宓,文章上佳,口若悬河,是为状元之才,也是我朝第一个女状元,前几日殿试,朕看过她一眼……”
说着,她却不继续说下去了。
陶宁疑惑看过去:“嗯?”
秦央忽然笑了一声,捏住垂下的发尾,挑了一下陶宁的下巴:“生的眉清目秀,是个机灵相,想来是栋梁之才。”
陶宁捉住她的手,将人拉近:“殿试学子众多,陛下何故只记得状元一人,这让臣甚是惶恐,恐人老珠黄,色衰爱弛了。”
秦央退开怀抱,嗔怪看了陶宁一眼,转身要进暖阁里:“去你的,你小我三岁,你人老珠黄,色衰爱弛了,那我算什么?”
陶宁起身追了上去,殿中宫人们仍侍立在原地。
这时候是不需要追上去的,陛下已经不需要人伺候了。
暖阁就在偏殿处,并不远,三步并作两步就将人追上,将人拦腰抱起,继续往暖阁走去。
把人放在床上,秦央还想说什么,就见陶宁从袖中抽出一方红帕,盖在她头上。
秦央瞬间无话了,眼前一片绯红,盖头后陶宁的身影若隐若现。
看了一眼天色,陶宁说:“婚礼都在傍晚,时辰也差不多,今夜就当是新婚之夜。”
不知为何,秦央隔着盖头往外看,胡闹似的一方红帕,还真把她盖成新婚之夜害羞的新娘了。
陶宁郑重地揭下红帕:“揭了盖头,就是妻妻了,好像除了拜天地,还会剪下一缕头发编在一块,意为永结同心。”
秦央眼前视线一亮,她伸手:“剪刀呢?”
陶宁一摸身上:“剪刀没带,用匕首可行吧。”
秦央想了想,她也不知道暖阁里哪有剪刀,便觉得可行。
一人割下一缕头发,放在一块,木盒被合上,珍而重之地收了起来。
秦央双眸潋滟:“那合卺酒呢?”
不说还好,才想起忘了这事,陶宁总不能说一时高兴,忘了这事。
毕竟她也才第一次成亲,没好意思去问旁人,自己摸索着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