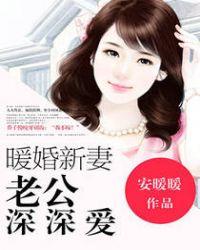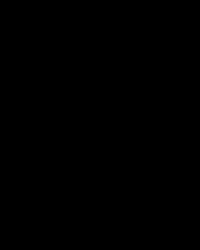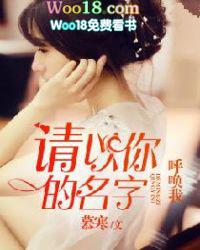落秋中文网>我的依洄 > 4050(第20页)
4050(第20页)
它先让患者进入一种深度放松的状态。在这种状态下,患者对于外界刺激的敏感度降低,松懈心防,心理医生趁机介入,诱导出患者潜意识的记忆,从而进行心理干预。
这种催眠疗法,在治疗焦虑症、创伤后应障碍中有明显效果,但效果大小,因个体差异而异。有些人容易进入状态,有些人则很敏感,不容易被催眠。
因此该疗法一直存在很大争议。
疗法没有统一标准,全靠心理治疗师丰富的个人经验。
梁泽更偏向标准化、模块化、有数据支撑和科学验证的治疗方案,无奈传统方法没有效果。
靳平春倒是投了赞成票:“我之所以推荐这家诊所,是因为明蓝医生和她团队2008年去过汶川,在四川待了很长一段时间,帮助震后的伤员群众做心理疏导,我相信她们的经验。”
梁泽夜里抱着岑依洄,问她,要不要试试?
岑依洄对明蓝诊所颇有好感,同时也是抵不住每夜失眠的煎熬,便点了头-
诊室里,弥漫一股淡淡的薰衣草香。
岑依洄躺进带按摩功能的治疗椅,明蓝医生坐在旁边,将椅子调整到舒适角度,“依洄,先深呼吸,慢慢地放松身体。”
岑依洄闭上眼睛。
“你正行走在一片宁静的森林里,清晨时分,阳光透过树叶洒在你的发梢、肩膀、衣袖,”明蓝医生的声音空灵遥远,“你的耳边有溪流声,鸟叫声,来,再深呼吸一次,让新鲜空气缓缓进入你的肺部……”
岑依洄渐渐摒除脑内杂念,进入一种放松状态。
意识仿佛抽离于躯体,独立于心理医生编织的美好梦境。
明蓝医生睨了眼岑依洄的心率检测屏,引导她进入下一步:“在那片森林里,你是主人,你可以控制树木生长的速度,也可以控制风霜雨雪的降临。没有任何事物引起你的恐惧,你是安全的,你非常安全。”
听到“恐惧”二字,岑依洄眉头轻蹙,呼吸稍稍变得急促。
明蓝医生注意到微变化,追问:“怎么了?你在发抖,是有你控制不了的恐惧吗?”
岑依洄眼皮动了动。
明蓝医生顿了一下,兵行险招:“如果你觉得那片森林不安全,我们换个地方,好吗?”得到岑依洄的应允,明蓝医生加强了空气中的氧浓度,“换个地方,你依然有控制的能力,不要害怕,我陪你一起过去。”
“往前走,一直走……”明蓝医生说,“我们走回到2011年3月11日,你和你的朋友苏睿,在仙台一间文化馆里跳舞。”
岑依洄脸色倏变,身体不自觉地发抖,随时有苏醒的迹象。
明蓝医生抓住她的手,坚定地反复强调:“你有控制的能力,所有事情都以你的意志发展,告诉我,你在恐惧什么,那个东西立马就会消失,说出来吧,说出来就没有恐惧了……”
岑依洄的脸上闪过一丝痛苦:“眼睛……有好多双眼睛在看我……不要看我……”
明蓝医生立刻记下新线索:眼睛。
“好的,盯着你的眼睛已经全部消失,你彻底安全了。”明蓝医生轻轻拭去岑依洄眼角的泪花,“还记得那些是谁的眼睛吗?他们不能再伤害你,你可以说出来。”
“不记得,不认识,”岑依洄悲伤地睁开眼,“我不认识。”
治疗戛然而止。
门开,梁泽被允许进入诊室。
他在外面就听到了岑依洄的呜咽,也顾不得明蓝医生和助理在场,弯腰抱住治疗床上的岑依洄,低头亲了亲她的额头:“还好吗?如果很难受,如果不想坚持,你可以喊停治疗。”
明蓝医生:……家属有时候真的很耽误事。
好在有了新线索,岑依洄说出恐惧的是“眼睛”。
明蓝看过日本当地的地震报道,岑依洄和苏睿被困的那间文化馆,有许多音乐厅观众遇难。岑依洄说“好多双眼睛”,大概率是那些遇难者。
难道岑依洄恐惧的根源是害怕那些遇难者的死状?
明蓝医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,但在结论末尾打了个问号。
结果显示,催眠疗法对岑依洄是有效的,她本人也有恢复健康的渴望,同意继续治疗-
时间不经意间步入夏天。
梁泽一门心思扑在岑依洄身上,梁世达约他几回吃饭,都被他找借口拒绝。中途回过几趟北京,修改论文,处理学校剩余杂事,接着便是毕业答辩和毕业典礼。
“依洄,跟我去北京吗?”梁泽洗完澡,上了床,“我一起订票。”
岑依洄经过一段时间催眠治疗,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。倒是想去北京,但分身乏术,她正在水深火热的期末周里渡劫。
“而且考完还要去见明蓝医生。”岑依洄遗憾道,“梁泽哥哥,提前祝你毕业快乐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