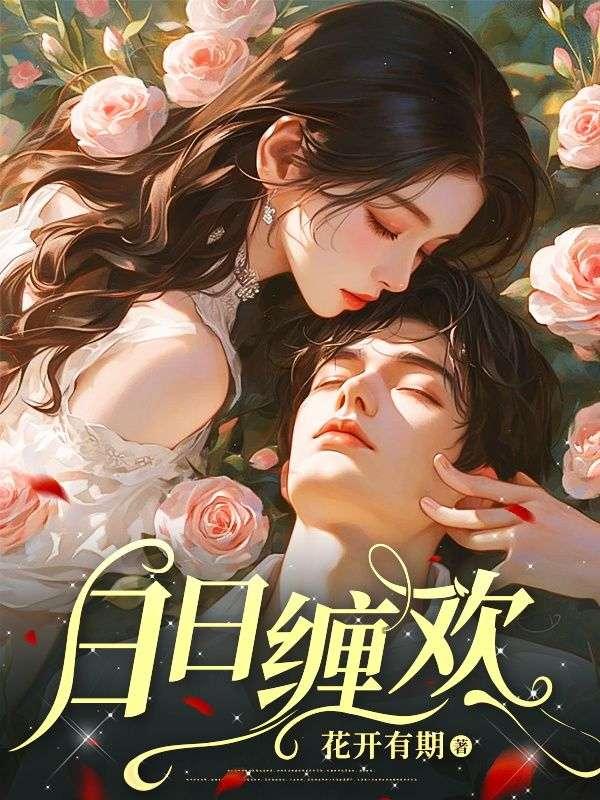落秋中文网>冲喜后,亡夫他又活了 > 第80章 番外 if竹马幼时便相识下(第3页)
第80章 番外 if竹马幼时便相识下(第3页)
那日他等到很晚才去沐浴,在浴房遇到了个不太熟的士兵。那士兵一开始只是远远盯着他看,后来便凑到了他身边,热情地说要替他搓背。
在被喻君酌婉拒后,对方未经允许直接上了手。喻君酌已经十五岁,在营中也听到过一些传闻,知道有人会喜欢男子,是以对这种接触颇为敏感。
男人的手抚过他脊背时,压根不是正经要帮他搓澡的姿态,反倒带着点不正常的暧。昧。但喻君酌也不是吃素的,他在营中待了数年,看着瘦削其实武艺并不差。
于是他一手擒住男人手腕,直接将人狠狠掼在了地上。
“我说不必,你是听不见吗?”喻君酌冷声道。
“不愿意就算了,没必要这么大反应吧。”那人开口。
“下次你再乱伸爪子,我就废了你的手,眼睛再乱瞟我就抠了你的眼珠子。”喻君酌一手将他脑袋磕在浴房的地上,而后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原以为此人心虚会就此作罢,没想到对方竟倒打一耙,污蔑喻君酌勾。引自己。这话传到喻君酌耳中时,他倒是没什么反应,却把一旁的章献气得够呛。
“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长什么样,我比他英俊多了,君酌跟我洗澡都不勾引我,凭什么会勾引他啊?”章献情商智商都不太高,本意是想护着喻君酌,说出的话却令人哭笑不得。
“你快闭嘴吧。”谭砚邦瞪了他一眼。
一旁的周远洄始终不发一言,只眸底的冷意越来越浓。
“此事是我处置不当,致使他手腕脱臼……”喻君酌开口。
“跟你没关系,若是换了我直接让他断子绝孙。”谭砚邦道。
“传令下去,营中若再有骚。扰、欺。辱、污蔑同僚之辈,一律杖责五十逐出大营,若有恶意侵。犯,直接杖毙。”周远洄终于开口,“谭砚邦你去查,此人这般明目张胆,想来不是第一次了。若是再有人指正他,便从重处置,给营中儿郎一个警示。”
谭砚邦当即领命而去。
“君酌往后跟着我一起洗澡吧,有章哥在保准没人再敢乱来。”章献说。
周远洄瞪了他一眼,说:“你去帮着谭砚邦一起查,看看营中是否还有此类情况,一律上报。”
章献不疑有他,领命去了。
营房中只剩喻君酌和周远洄。周远洄盯着少年看了一会儿,无奈叹了口气:“往后你每日沐浴时跟着我一起吧。”
喻君酌点了点头,没再多说什么。
自那以后,喻君酌每晚洗漱都跟着周远洄。洗澡时,周远洄会将他安排在浴房最靠里的位置,自己则挡在他外头。但不知为何,喻君酌提出要帮周远洄搓澡,对方从来都是拒绝,也不愿帮他。
喻君酌没人互相帮忙搓澡,只能自制了一条长长的布巾,放在背后像拉锯似的自己给自己帮忙。
周远洄为什么不愿帮他搓澡?
这个问题喻君酌想了很久,没得出结论。
后来他无意中和章献闲聊,隐去人名旁敲侧击询问了章献的看法,章献一脸了然的表情,说:“这还不简单吗?生怕遇上断袖呗。像我从来不喜欢给其他人搓澡,也不愿让别人帮我。”
原来是这样吗?
喻君酌想起了先前那件事。
周远洄会不会怀疑他也有点断袖的倾向,所以才会日日拉着他洗澡,避免他和别的儿郎接触?因为提防介意,这才不和他互相帮忙搓澡。
这么一想,好像很合理。
那日之后,喻君酌特意找了个机会,朝周远洄澄清了这件事情。他澄清的方式很简单,朝周远洄说了自己未来的打算,如何成家,如何找个心意相通的夫人云云。
周远洄听了这些话没做评价,喻君酌也不知是否奏效。
在营中这几年,喻君酌的性子已经改变了不少,不会再因为这些有的没的烦恼不休。他自认表明清楚了立场,又问心无愧,在面对周远洄时便十分坦然,毫无芥蒂。
周远洄怎么想,他不知道也不干涉。
这一年入秋后,大渝和南绍的战事陷入胶着。
“君酌!”这日谭砚邦匆匆找到喻君酌的营房,开口道:“你快去看看殿下吧,今日殿下气得不轻,我是真怕他不管不顾地杀去南绍。”
“出什么事了?”喻君酌问。
“南绍人不知道发的什么疯,竟然不顾自己人还在战场上拼杀,直接放了毒烟,害得不少人当场就毒死了,中毒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。”谭砚邦愤愤道:“他们可真够狠的,这毒烟一放,他们自己人死得比咱们更多,少说也得数千人。”
“咱们死了多少,伤了多少?”喻君酌问。
“因为毒烟死了至少三千有余,中毒受伤的估计过万了。”谭砚邦说:“我听军医那说法,若是找不到解药,中毒受伤的士兵熬不过七日。”
周远洄素来爱兵如子,无论是战场拼杀还是平日在营中,都是和士兵们一样不分彼此。此番这么多士兵死伤,他心中定然恼火,难保不会做出什么极端的事情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