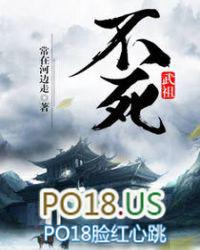落秋中文网>阶上春漪 > 90100(第7页)
90100(第7页)
苏妙漪知道他在说台上的“公子哥”,冷哼了一声,“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
容玠默然片刻,言简意赅地给出评价,“……当真是面目可憎。”
“……”
苏妙漪唇角抽了抽,有些想要上扬,但又被硬生生压平。
正当她别开脸,与自己的表情作斗争时,容玠搭在扶手上的手一使力,径直将她连人带着椅子一起转了过来,避无可避地对上他那双仿佛能将人溺毙的眼睛。
“可是妙漪,我一直都那么面目可憎吗?”
容玠轻声问道。
“……”
“台上只有寥寥几出戏,台下我们却朝夕相伴了数月。如今在你的记忆里,卫玠就只剩下这些面目可憎了吗?”
容玠低垂着眼,凝视着苏妙漪,嗓音虽低沉却柔和,轻易便冲破屏障,叫人不得不静下心来听,“我们虽有误会有争执有裂隙,可我们也有过那些柔情蜜意、如胶似漆……看客们不曾得见,那你呢?真的也都不记得了?”
苏妙漪一怔。
耳边是戏台上弄竹弹丝的乐声,眼前是容玠那双乌沉幽深只映着她的眼睛,她不自觉就被牵动心神,在脑海里搜寻着那些被隐去的点点滴滴:
是卫玠醒来睁眼后,第一次相撞便缠绕在一起的视线;是第一次并肩坐在窗下抄写小报时不小心触碰、又很快分开的双手;是见她炎夏时总是拿小报扇风,所以用本就微薄的工钱买给她的第一把团扇;是因为一个书院学子对她言语冒犯,第一次发脾气挥出去的拳头……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呢?
好像是从他们定亲后,左邻右舍开始风言风语,来往书肆的人也开始阴阳怪气。好像所有人都看不惯他们在一起,不是说卫玠孤僻冷淡、待她没有真心,便是说他穷酸落魄、实非良配。
苏妙漪不知道这些话有多少落进了卫玠耳里,但似乎从那时候开始,那双乌黑剔透只映着她的眼睛逐渐多了一个复杂而浑浊的漩涡,漩涡里滋生出了嗔、怨、哀、怒……
而此刻,那个漩涡消失了。坐在她面前与她四目相对的,又变成了那个满心满眼都是她的卫玠。
“呔!你这勾魂的狐妖——”
戏台上,一声锣响,一声怒叱。
苏妙漪眸光一震,猛地回过神。
她飞快地往椅背上靠去,拉开了与容玠的距离,整个人也像是从他掌控的回忆里挣脱,“……你我是结义兄妹,且我已有婚约在身,容相还是莫要说这些引人浮想联翩的话了。”
“……”
容玠仍维持着俯身的姿势,唇瓣动了动,似是还想要说些什么。
苏妙漪却斩钉截铁地打断了他,重新看向戏台,“看戏吧。”
直到察觉那道视线从自己脸上移开,苏妙漪的眼神才飘忽起来。
不对劲,太不对劲了……
容玠这三年去青州到底是在做官还是在修炼?
成精了吧?!怎么连她都给蛊进去了?
接下来,二人都没再说话,似乎都沉浸在了戏里。
直到台上的戏唱到了公子追悔莫及,在渔女要另嫁他人时,终于低下了他高贵的头颅。当着所有人的面,公子用双膝跪走到了渔女跟前,红着眼求她回头。
眼见着翊官那张俊朗的脸布满泪痕,苏妙漪忽地呛了口茶水,连忙别过头,用帕子掩了唇轻咳两声。
这一刻,她倒是理解了江淼那句“脆弱和眼泪就是男子最好的嫁妆”。
容玠原本已经有些困倦,被她这么一咳,困意不翼而飞,转头看过来。
苏妙漪掩饰地皱了皱眉,吐出硬邦邦的两个字,“好、癫。”
容玠眸光微动,再看向台上癫狂成一团的人群时,眼神里倒是清明了不少。
“……像他这般,便能收回覆水、重圆破镜?”
容玠若有所思。
苏妙漪瞬间寒毛耸立,一口否决,“这是江淼的个人癖好。若换成我,断然不会喜欢这种哭哭啼啼、动辄下跪的做派!绝、对、不、会!”
半晌,容玠才颔首,“知道了。”
随着台上的翊官以身入局、以死相逼,渔女终于还是与他重归于好,满堂欢喜,大幕就此落下,折磨苏妙漪的“酷刑”也总算告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