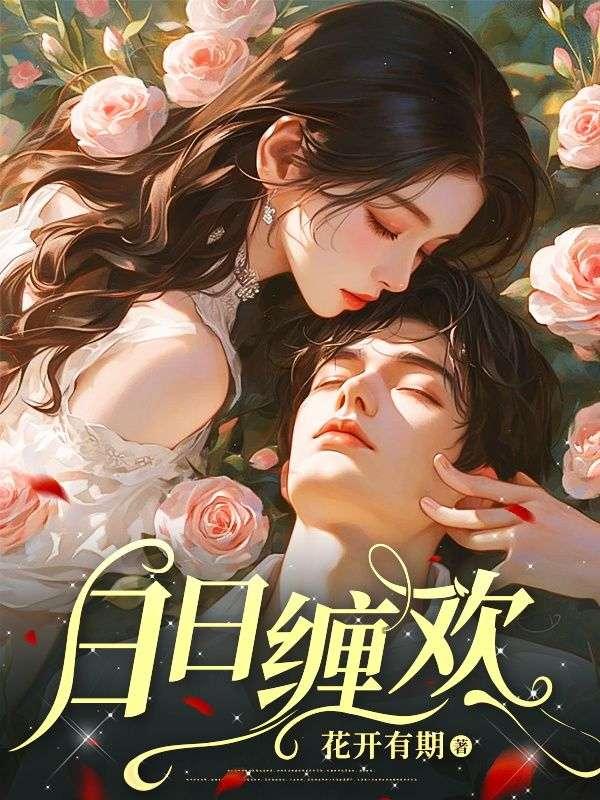落秋中文网>重回落魄皇子登基前 > 4050(第22页)
4050(第22页)
且看那娘子身上所穿,上等花锦,一匹十几两,可不就是大户人家?而那男子穿粗布,跟他们店里小二没差,显然就没她好。
这两人大过年的不在家,掌柜稍猜便晓得了,一定是私逃。
没准男的是长工、家仆,凭一张好脸就勾引了主家小娘子,啧啧,真是世风日下掌柜不动声色,心下忍不住鄙夷。
夏侯尉以为人不愿说,蹙了下眉。有钱才能吃得通,他只好拿出银裸子:“够么?”
“够够够!”掌柜突然高兴地接住,“长工哦呸呸呸,大主顾,您问我真是问对人了!说起抚州游玩的去处,可没人比在下更清楚!”
掌柜收了银子,讲起话来滔滔不绝。
他一连说了好几种去处,神仙庙、梅花园、瓦子、姻缘桥褚卫怜喝茶听着,似乎没个让人提起兴致。直到掌柜提到了雒江画舫,褚卫怜双眸忽亮,似惊奇:“寒冬了,竟然还会有画舫。”
“有呢。”掌柜眯眼笑:“只要雒江不结冰,就有画舫。只是近儿岁旦,天又太冷,夜里很少有游人会去坐画舫,所以没有那么热闹。”
“小娘子若想去,不如等入春了再去,那时候画舫才叫多呢,还有坐篷船的歌女们弹琵琶。”
褚卫怜摆了摆手,叫掌柜走。屋门重新关上,她支起下颌看他:“不如就去坐画舫吧,我已经很久没坐过画舫,这会儿倒有点馋了。反正我们日后也不会再来抚州,咱们再带只暖炉去,江上看雪一定很美。”
夏侯尉想了想,点头应下。
就像褚卫怜很久没坐画舫,他也从未和她乘过船。虽然他不好这些玩乐,觉得它们乏味,但和她一块他很乐意
隔日入夜,褚卫怜坐着马车到了雒江。
雒江是中原数一数二的江流,一望无涯,抚州人将它分作了两半,一半用来游玩赏景,于是在江边修了数座湖亭,还有画舫、楼船、乌篷船等各种船只;另一半则作为抚州的渡口,停泊了许多载货的大船。
夜凉如水,寒风簌簌,因为正月初一的缘故,在外漂泊的商客也少,货船便用不上,一艘艘寂寥地靠于岸边。
靠近雒江的堤坝,零星分布了几家摊贩,有卖零嘴的、卖花的、还有卖汤炉的。
“烫羊肉,姜辣萝卜,热乎的羊肉馄饨,来瞧一瞧”支起篷布的摊子边,有个老妇在叫卖。她的相公则在炉子边烧火。
今夜的游人很少,褚卫怜闻声,便远远看到了老妇——是奶娘,果然是她的奶娘!方才听声儿便觉得耳熟了。没想到大哥还把奶娘带来。
看见熟人,褚卫怜逐渐觉得心安。
“饿吗?要去用碗烫羊肉吗?”冷风里,夏侯尉问她。
此人素来阴险,眼多识怪,褚卫怜生怕给他瞧出端倪,因而摇头。“我果腹过了,不算饿。你若饿咱便去吧。”
“我也不饿。”夏侯尉笑道。
今夜来雒江他还带了暗卫,但没有全带,褚卫怜不知道有多少个,他的暗卫各个都和末伏一样,总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不过她已经把夏侯尉引来雒江了,剩下的事就靠哥哥。
黑色昏暗,江边停泊着五艘流光画舫。浩瀚的江面卷着天涯雪,冷风呼呼,褚卫怜拢紧了斗篷和他过去。
管画舫的,是个佝偻背的老头,夏侯尉问道:“店家,我们借只画舫多少钱。”
“你们要游多久?”
褚卫怜说:“半个时辰就好了。”
寒风灌面,老头咳了咳,粗着嗓子:“一百二十文。”
褚卫怜兜里是没银子的,她戳了戳夏侯尉。
夏侯尉摸向袖口,正待取钱,忽然眼前寒光,直刃飞刺。他脸色大变,侧身闪过,那老头竟然挺起腰板,不再佝偻,面露凶恶,又是一刀朝他刺来!
他来不及多想,三两下拽过褚卫怜,于此同时,江堤下竟突突突跳出许多黑影。
这些刺客,远比他带的暗卫多的多,皆穿夜行衣。二十多个人纷涌而上,突然,一只飞镖顺着寒风直直扎进他的后背。
血漫衣衫,夏侯瑨疼得咬牙,也没精力去想这些人的来路,只抓了褚卫怜的手拼命往前奔。夜色晕眩,他的暗卫们已经纷纷出来,朝对方挥刀。
褚卫怜跑得气喘,寒风灌袖,冷得她瑟瑟发抖。突然,夏侯尉肩臂一沉,她感觉有什么东西落在她的脸颊,是热烫的,从脸颊蜿蜒至脖颈。
禇卫怜伸手去摸,竟是黏腻的液,是血,是夏侯尉的血。她还没来得及转头,突然被他推上了马车,“走,快走!”
她跌坐车里,他站在车下,狂风吹开他脸边的落发,嘴角惨烈的血,蜿蜒而落。
夏侯尉用力抽了马臀,马儿惊蹄飞奔,赶马的正是小道士末伏。
寒风萧瑟,没出两里路,末伏突然恶狠狠地回头,瞪她,杀意毕露。
褚卫怜吓得攥紧拳,正要抓簪子,末伏突然甩开缰绳,跳下了马车,竟是朝夏侯尉的方向跑去!